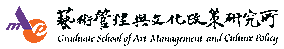文/陳惠儀 圖/羅慕昕
去年在藝政所第一週上課,經常會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唸藝政所?我一般會說「在香港從事多年的藝術村劇場工作,幾年前有機會到倫敦和柏林交流和短期策展,讓我對藝術管理的工作產生了撞擊,覺得是應該調整未來的工作方向的時候了,於是我開始尋找,尋找一個可以幫助我從過去的藝術文化實務工作進入的研究領域,且能夠透過系所的課程讓我專注於我所關心的命題進行深度的思辯與總結。我向香港藝術發展局申請了海外進修獎學金,然後我決定來到台灣這個與香港脈搏相近的地方,我在網上找了三個系所,問了一些朋友的意見,鎖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及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班,經過香港一輪複雜及惱人的行政程序,最後成為首名錄取。」以上說法都是事實,但我想再誠實一點:
1)離開香港但不會太遠,台灣就很方便回港
2)聽說藝政所可以看很多書和論文,豈不悠哉,還不用花錢
3)我懶惰不想工作,我不想進入劇場了
結果入學一年多後,的確台灣回香港很方便,特別是現在香港抗爭運動時期,只要能力許可我便衝回去;藝政所真的是可以看很多書和論文,而且是很艱深的書,我自認自己很熟悉莎士比亞嗎?上週聽到趙慶河老師所談的莎士比亞,下課後我只好垂頭默默回家重讀《哈姆雷特》;我真的要離開劇場嗎?今年十一月我與廣藝基金會一起策劃黑盒劇場香港週,邀請了三個不同的團體來台灣演出。這是一個驚人的十一月,我體驗了邊唸藝政所邊工作之分裂時刻,但同時,我又看到二十年前初入劇場的自己。
劇場與人的相互映照
我與台灣的第一次結緣是2000年參加了香港藝術中心舉辦的「次世代青年藝術節」演出,此作品被送到台北的牯嶺街小劇場重演,當我第一次踏入台灣這個當時最火紅的小劇場領土,過去在DVD裡看到的表演團體如渥克、莎妹、臨界點、優劇場等等前輩一一實體盡在眼前。還記得第一天到達牯嶺街小劇場時,我們幾位年輕人正準備更換衣服開始排練,場館人員給我們每人掃把和拖把,首先是要一起清潔劇場,當時我心裡不免抱有懷疑,就像是一個飯來張口的小孩心不甘情不願要用力提起餐具一樣,我們邊掃地,場地人員開始將場地逐點逐點引路,每個出入口的設計、觀眾席的分佈、空中與地面的高度、破爛了的建築安全注意等等…接下來每天排練前我們都打掃,漸漸發現打掃是很暖身的運動,我開始對場地每個角落提高意識,我們開始在原有的創作上,加入場地空間的變化進行再創作,放棄把香港演出一式一樣的重演的計劃。
演出後輪到台灣劇團進場,我看到他們全團一起裝舞台燈到杆子上,我問「你們不是演員嗎?」他們說「是呀,但也可以幫助裝燈。」這件事再令到被寵壞的小孩口裡的飯吐出來,小孩明白到,不是不追求個人專業,而是小劇場的魅力和影響力就是一種互動的能量,這不僅僅是指創作上的自由奔放,而是作為製作人,我更開放了一個製作的心,我開始學習「愛場地」才能使創作得以更優美地發揮,更能充分幫助劇團創作人實現他的構圖,於是我回到香港開始在前進進牛棚劇場東摸西摸、爬高爬低,對小劇場承諾,有我一日也要將小劇場做好,從此就在劇場工作十八年了。
從香港到臺灣–黑盒子小劇場的策劃

今年重回台灣策劃演出,與廣藝基金會合作,無論場地器材設備和專職人員都是成熟專業的表現,但同時也保持著一顆開放的心,一一將可能與不可能的構想成真。策劃初期,我與劇場經理討論創作的想法,腦力震盪過後,我們決定再嘗試把廣藝廳劇場變為黑盒小劇場; 把原定一個演出改成密集式三個演出,成為廣藝廳十一月的香港主題月。「香港週」策劃選取演出的前題是過去香港最近期的作品,主題上有多次改動,最後我們決定了邀請李國威、梁菲倚和甄拔濤三位風格強烈的導演參與。與各導演選節目時,我們沒有特別為了在台灣觀眾口味而配合,李國威去年執導大衛.馬密九十年代力作《奧利安娜》,這劇本過去在世界各地都搬演多次,但在澳門上演時,就如藝評人鷺兒所說「現時的性別議題乃至其他議題的發展已跟九十年代的「男女平等」有所分別,但文本想要探討的權力關係歷久常新,如何引領觀眾思考當中的拉扯在今日的意義,正是今次創作團隊的挑戰。」演出後觀眾討論果然最為熱絡,也有觀眾說「一直到下半場的中間,才驚覺原來自己對於性別歧視居然是已經習慣。」
第一次見梁菲倚的演出是1997年的《飛吧!臨流鳥,飛吧》,那是當時香港一系列「97劇」的重要作品,我人還在銀行工作,下班後進入劇場當觀眾,就如很多上班族一樣,看不明白但情緒很激動,在演出中只看到一切不能預料的未來和一個一個埋入沙堆的現況。原藉馬來西亞的梁菲倚當時剛在演藝學院畢業,之後來她加入台灣優劇場演出,去年回港出任母校戲劇系講師,隨即帶著同學生以半讀半演的方式重演此劇,所以當我決定找菲倚來台灣時亦鐵定是《飛吧!臨流鳥,飛吧》,我相信由香港青年回溯當年97過度的情境絕對是現在最需要被聽到的聲音。
而甄拔濤則是近年香港最活躍而又多線發展的藝術家,也是首位入選柏林藝術節劇本市集的華人編劇,他的創作領域廣闊,在編導大型藝術節作品《未來簡史」同時亦創作出充滿思辯的語言文化的《如何向外星人介紹香港人的感情生活》 的小劇場小品,此劇以老師講座的型式欺騙觀眾進入演出,玩味的文字似是而非的引進一段愛情經歷,重踏遍香港多個習以為常的約會地點,配合台灣視覺藝術家丘智華鏡頭下的城市景觀,最後因失戀來到台灣散心。
三個演出的決定都在今年二月敲定,經歷團隊人員整合、製作補助申請、排練及製作籌備,萬萬想不到同時也經過抗爭運動的洗禮,九月時還通過多通電話,討論能否如期演出,十月時再多次討論擔心香港團隊不能出國,十一月初已有棄演緊守香港的聲音,最後,演出如期進行,讓我在這個翻天覆地的十一月再次踏入台灣劇場。
研究所的知識涵養

在台灣的製作工作開始時,我需要一位藝術行政伙伴幫助共同工作,而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藝政所的同學,而這決定最後顯然是絕對明智之舉,因為不管在時間配合上和遇到問題時,也有準確的解決方法。默契是一直蘊養發酵的,對於藝術管理的經營理念和實際考慮,是如此的心照不宣,同時就像是20年前一起起步。
我在藝政所這一年的學習獲益良多,課程讓我能夠從過去的藝術行政工作對自我進行反省、整理與推進,在指導老師的帶領下,進入研究者的身分角度對藝術家的創作歷史深入探索與描述。在學習的同時我還進行得非常高密度的演出製作,在風雨飄搖的時代下順利完成,這一年有賴老師與同學們共同努力,成為我未來20年的人生方向。
發表於2020 年 01 月 08 日